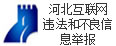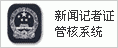專家參觀雄安新區(qū)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陳列室內的標本,。
本報記者 韓梅
“多年考古勘探發(fā)掘確認,,南陽遺址時代為戰(zhàn)國中晚期,包含一大一小兩個城址,,時代跨度2000多年,,是迄今為止雄安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古城址類遺存,開啟了雄安新區(qū)的城市時代,。”近日,,在“京津冀協(xié)同發(fā)展:燕文化考古雄安對話交流活動”中,雄安新區(qū)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負責人雷建紅接受記者采訪時說,。
主體為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
在雄安新區(qū)容城縣城東14公里的晾馬臺鎮(zhèn)南陽村村南,,規(guī)模宏大的南陽遺址映入眼簾,工作人員正在探方內作業(yè),。
這是一個“凸”字形遺址,,北高南低。小城居北,,平面呈方形,,邊長200米;大城居南,,平面呈矩形,,南北500米,東西600米,。
南陽遺址已基本確認其主體文化面貌為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,,遺址內已發(fā)現(xiàn)的一大一小兩座戰(zhàn)國城址的布局和建筑方式日漸清晰,為研究燕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,。
大城建成時代略晚于小城
遺址內大城的西城門,、南城門位置已得到確認,并發(fā)現(xiàn)了城門附屬道路,。在“凸”形遺址西北部1600米處,,還有一處墓葬區(qū),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均有典型的燕文化特征,。
“墓葬和城址的并存發(fā)現(xiàn),,進一步證明了南陽遺址的年代和遺址性質。”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傅永超說。
“兩座城的建筑方式也有進一步發(fā)現(xiàn),。”傅永超介紹,,大城城墻下有基槽,基槽底部有兩條倒梯形的小基槽,,而小城城墻下沒有基槽,,城墻內外修筑護坡以加固。此外,,大城的北城垣利用了小城的南城垣,,是在小城的南城垣基礎上夯筑而成的,表明大城的建成時代略晚于小城,。
遺址內兩座城址的發(fā)現(xiàn),,不僅為白洋淀地區(qū)東周和漢代城市起源、形成,、發(fā)展等城市化進程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載體和范例,,而且推進了該地區(qū)先秦時期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演變、人與生地互動關系的研究工作,。
2017年5月,,雄安新區(qū)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揭牌,開啟雄安新區(qū)文物保護的序幕,。截至今年上半年,,雄安新區(qū)已開展專題考古10項、基本建設考古23項,,勘探面積達682萬平方米,,發(fā)掘面積2萬多平方米,出土文物4000余件,,確認不可移動文物263處,,其中包括南陽遺址。
263處遺存分4個等級保護
雄安新區(qū)建立了文物遺存分級保護體系,,將登記確認的263處各類文物遺存初步劃分為4個等級進行分級保護,。
2017至2018年,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(lián)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,、中國國家博物館,、中國文化遺產(chǎn)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組成9個雄安新區(qū)聯(lián)合考古隊,對雄安新區(qū)規(guī)劃全域33個鄉(xiāng)鎮(zhèn)的640個行政村進行了系統(tǒng)的考古踏查,,共登記各類文物遺存共計263處。
經(jīng)考察,,這263處遺存年代自新石器時期延續(xù)至近現(xiàn)代,,文物遺存涵蓋城址、聚落址、墓葬,、窯址等,。“我們根據(jù)其分布范圍、文化內涵及性質,,并參考保存狀況,、豐富程度、考古價值,,經(jīng)專家最終審核,,將263處文物遺存初步劃分為A、B,、C,、D四個等級進行保護。”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曉崢說,。
通過文物遺存分級保護,,將文物保護與新區(qū)建設結合起來,不僅讓文化遺產(chǎn)在雄安新區(qū)建設中得到傳承和發(fā)展,,也為雄安新區(qū)的工程建設贏得了時間與空間,。
據(jù)悉,雄安新區(qū)考古調查采用系統(tǒng)和精細區(qū)域系統(tǒng)考古調查方法,,關注古今環(huán)境信息綜合分析,,廣泛采用了航測、RTK(實時差分定位)測繪,、GIS(地理信息系統(tǒng)),、三維掃描和影像重建測繪新技術,考古科技含量不斷提升,。